梦回廿八都
梦回廿八都
江 山

廿八都是我心中的一个梦,长久醒不过来。
为写《江山多娇》这本书,2007年春节和国际劳动节期间我都回故乡采访时,江山市文艺界的朋友都拿出写廿八都的书和摄影集给我看。也许脑子里接收到太多廿八都信息的缘故,当天晚上我竟做起梦来,梦见自己去了一趟廿八都,而且竟是坐船去的,船又不在水上行,却像在云里雾里飞一般,最后降落在廿八都附近浮盖山的三叠石峰上,您说有趣不有趣?
第二天坐在江山开往杭州的列车上,我又想起了昨晚去廿八都的梦。实际上廿八都我去过两次,而且都留下了不同的印象,长期珍藏在自己的脑子里。倒是这个梦促使我打开手提电脑,在列车上写下了这篇散文圆梦。

我第一次到廿八都是偶然路过。那是1974年的夏天,在读高中的我趁放暑假,便到福建省浦城县忠信公社的亲戚家做客。去的时候是通过在浦城县汽车保养场修汽车的堂哥徐怀忠介绍,搭福建省浦城县运木头到江山贺村返程的货车去的(当时能搭个便车算是够有面子的事),可一路上有三道岭让我提心吊胆。
第一道岭就是临近廿八都的小竿岭,汽车在岭背上时,廿八都尽收眼底,令人感到像在飞机上看大地一样眼界、心胸异常开阔。再往前开则全是下坡,汽车在“S形”的盘山公路上往下滑,司机双手紧握方向盘,一只脚踏在刹车上,车窗外不时地响起刺耳的刹车声。大约滑行了近10里路才到岭底,我已被吓得脸色都有点发青了。后来往前开,又翻过五显岭、滑下鱼梁岭,都有类似的惊险,但我已经不太怕了。
廿八都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在一个三叉路口我看到有一块水泥牌子写着浙江界、福建界、江西界,并标有三个红色的箭头。我们的车子朝着福建省浦城县地界前进,第一次出远门的我当时出省跟现在出国一样感到挺神秘的。
在亲戚家玩了一个星期后我就回家了,没有便车搭,我便先走到离忠信公社较近的一个叫松溪的地方,去换乘浦城开往江山的客车。当时交通极不发达,从浦城开往江山的客车每天只有一班,早上开出,下午返回,再就没有别的客车可坐了。我赶到松溪汽车站后,车票早已买完。怎么办,我正在发急之时,突然听到有人在候车室里讲江山话。我回头一看,背后站两位四五十岁左右的中年人,便与他俩用江山腔打了下招呼:
“大伯,你们也是江山人?”
“是呀,我是廿八都人;他是赵家人。我姓谢,他姓赵。小老弟你要去哪里?”那位年岁大一点的长着满脸胡子的大伯说。
“我想回江山去,可车站排队的人多买不到票了。”
“我们也想回去,也没买到票。”
“哪怎么办?”

“这一带的路我比较熟,我带你们先到俺家廿八都,再坐江山到廿八都的回程车去。”谢大伯说出了打算。
“行!36计走为上计。”赵大叔也认为这个办法最好。
接着我们3个人就沿着一条山道往山外走。谢大伯不仅路熟,而且还很健谈。他先向我介绍,他和赵大叔是同事,在松溪附近的山上做松香,就是将山上的松树像割橡胶一样先割开一道口子,让松树浓流进树下的毛竹筒里。装满后再一筒一筒收集起来,送到厂里放在火上炼,除去水分和杂质,一块块黄色的松香就炼成了。
“谢大伯,你为什么不带我们走汽车路,而走这条高低不平的山道呀?”我有点担心地问。因为我人生地不熟的跟他俩走,如果他俩产生什么念头,动起手来我一个小孩子根本不是他俩的对手,所以我保持着高度警惕,不走前面或中间,一直保持距离跟在他俩后面,还在路边找了根树枝以防万一。
“山道路近,而且这条山道是有名的仙霞古道,是古代黄巢将军率黄巾军修的。听我父亲等上辈人流传,修路的时候许多廿八都人是全家出动,挖土挑石,送茶送饭,有的人还在修路中受了伤,但仍坚持和黄巾军一起将路修好。”
谢大伯一路上讲着故事,一路上还常帮我背行李。他也看出了我的心思便向我介绍:“俺廿八都人勤劳朴实,邻里相处很融洽,有些人家外出不关门,也不会丢东西。所以,你不用担心我会把你骗去卖了。”

听了谢大伯的这番话,我放心多了。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山景如画的仙霞古道走了近4个小时,终于到达了廿八都。最先让我见到的就是古老的水安桥,桥上建有九间桥亭,中为重檐歇山顶,建于清光绪十七年(1891年),为浙西唯一的设有古桥亭的古桥梁。与桥下的枫溪和两边的青山构成了的一幅秀丽山水画,空中漂着一些淡淡的云雾,整个古镇就像在仙境、梦境中一样,真是美妙无比。
谢大伯带我们沿着枫溪老街到了他家里,他妻子热情地用高山茶、玉米籽、地瓜、野菜、腊肉、土鸡蛋、糯米酒等土特产招待我们。在谢大伯家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餐饭,他和妻子还把我们送到廿八都汽车站,直到客车开动还在路边挥手。那时候,我只看到廿八都有很多古老的房子,并没有想到日后会成为一个旅游之地,但我心里却记住那位廿八都好人——谢大伯。直到我参加工作后因采写稿件,与家在廿八都的江山市台办谢培松主任经常打交道时,我在对他感到非常亲切之际,自然会想起那次巧遇的廿八都好人。

前几年的一个秋天,我特意又去了一趟廿八都采风。与我30多年前第一次到廿八都相比,情况可用“今非昔比,换了人间”来形容。首先是路好多了,那年到廿八都的江浦公路是沙子路,一辆车子开过就是灰尘如雾;有些山路非常陡峭,像我那次从廿八都回来在小竿岭上坡时,就看见几辆烧木炭的汽车喘着白气“呼呼”大叫,却像蚂蚁一样在岭上爬得很慢很慢;现在则全是水泥路,而且很宽阔平整,在路上车速也快多了,尤其是那让汽车发抖的高高小竿岭已不用爬了,汽车直接可从隧道中通过(现在已变成了高速公路);再是车子多了,当年江山到廿八都的公共汽车只有一班,现在过十多分钟就有一班中巴车到江山城里,车子档次也比较高,人们进出方便多了。

如果说我第一次到廿八都感到那里的人好,那这次到廿八都见到的就是景美了。当我们驱车60多公里从江山城来到廿八都镇街头,迎面就扑来一股“旅游味”:只见一群上海的游客手拿照相机、小摄像机刚从车上下来,在举着小旗、握着小喇叭的导游小姐带领下正往枫溪老街里面走,我们也加入到游客的队伍中。
据导游介绍,廿八都是一块历史悠久的飞地,到三省交界处双脚一跨就可以踏在三省中的两个省里面,因此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早在汉代因廿八都一带因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汉武帝怕一旦造反不好收拾,将当地乡民都押往外地,成为“人迹所绝,车道不通”之地。自唐末黄巢起义军耗时两年开辟仙霞古道,打通三省交通后,这儿不但是军事要冲,从浙入闽、或从闽入浙,翻岭过关到达廿八都时正好一天,适应过往商旅的服务业遂兴旺起来。北宋熙宁四年(1071年)江山设都四十四,此地排行第廿八,得名廿八都,至今已有900余年历史。明代收复台湾的爱国将领郑成功和他的父亲,曾率部驻守过这里。到清朝时全国长期统一,加上四面关隘相守,很少受战乱影响,商业繁荣发达,鼎盛时每天有千根扁担在运货。外来客商、杂夫,流落的败兵、退役官兵,纷纷在此定居。据统计,廿八都全镇有800余户4000余人口,在廿八都数千人中,有132个姓氏,讲13种方言,操南腔北调的都有,廿八都的普通话还是比较标准的,所以称作“官话”。所以,这里也是全国各地语言、风俗的“大杂烩”之地。

一路走去,只见洵里和枫溪街上铺着石板或鹅卵石,走在上面充满野趣。街道两旁的民居古色古香,有的门板已经发黄发黑,呈现出历史的苍桑。其中,镇上曹、杨、姜、金"四大家族",在清末民初时名噪一时。曹家以经营田地为主兼开南货店、布店;杨家从经营竹山到造纸,以后转为南北货交易为主;姜家从经营油料到以开布行为主;金家从经商到以收租耕读为主。古镇重点保护的36幢古建筑中,绝大多数是这“四大家族”的宅院,仿佛在向游人讲述着勤劳节俭的发家史。

古镇里还有孔庙、大王庙、万寿宫、忠义祠、老衙门庭若、观音阁、大云寺等公共古建筑10多所。在这些众多的寺、庙、宫、殿中,以大王庙规模最大,孔庙最雄伟壮观。孔庙建于宣统年间,占地1500余平方米,整体布局沿中轴线依次为照壁门庭、正门、前殿、天井、正殿、天井、寝殿共计三进三天井,左右为厢房,以檐廊连结,结构上,明间均为抬梁式、边贴为穿斗式,正殿为两层重檐歇山顶楼阁,四面飞檐出挑,十分高大雄伟。建筑内以精湛的木雕艺术和丰富的彩绘最具特色,所有的梁、枋、脊标、天花板,均绘月山水、人物故事以及龙、凤、花、鸟等绘画作品,几何图形、牛腿、雀替、窗扇、栏板等木构件均有浮雕或镂空雕,题材丰富,形象极为生动,犹如一座艺术宝库。另外一镇有大小两个文昌阁,在国内所罕见,说明古代廿八都人就祟尚文化教育。文昌宫内,墙壁上、天花板上画有400多幅彩绘,神佛、人物、山水、鸟兽、鱼虫等不一而足,彩绘线条流畅,栩栩如生。走进水星庙里,安放着真武大帝和道教诸神;古戏台上,千百年来演绎的是一茬又一茬独特的民情民俗。那座有名的江西会馆,住的是东西南北八方来客和商贾,可见当时之繁华。2007年,廿八都已被列为中国历史文化名镇。

这次我还有个心愿,就是想去看看那位好心的廿八都好人——谢大伯。结果我好不容易找到他家得知,老俩口十多年前就仙逝了,他家的后人见到我只能是“笑问客从何处来”了。我聊了几句与谢大伯相识过程的话外,送了几本书给他们后就走了。

记者曾游过出过三国时期吴国之主孙权的富阳龙门古镇、蜀国军师诸葛亮后裔生存的诸葛村,清代乾隆皇帝做过行宫或到过江苏木椟及周庄、同里古镇,还有文学巨匠鲁迅写过的绍兴鲁镇和出过文学大师茅盾及木心的乌镇,那大多是一片张扬的水乡风情,而像廿八都这样深藏在山中的古镇,给人的是一派含蓄且少有的山乡风情,可谓别有风味。怪不得家在新疆的全国政协副主席阿不来提•阿不都热西提会对没有葡萄架的廿八都古镇赞叹不已,善于军事判断的福建军区原司令员皮定钧将军早作出了“廿八都会出名”的非军事结论,拍过电影《芙蓉镇》的著名导演谢晋名指张艺谋暗中婉惜自己没有把廿八都作为电影外景地,而以写小说为主的著名作家汪浙成却在游过廿八都后重采矿浓墨地将廿八都描绘成一个“遗落在大山里的梦”,解放军艺术学院副军级教授崔开玺在廿八都采风半月竟依依不舍回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奥运冠军罗雪娟的父亲罗国安当年曾下放在廿八都镇坚强村,江山是他的第二故乡,他因病从杭州中策集团朝阳橡胶有限公司内退后,从1999年开始就带着罗雪娟的母亲回到坚强村重新安家落户,后来他干脆租了田地种粮种菜,由于风景美,空气好,吃的东西没污染,两老日子过得健康开心。罗雪娟也多次到廿八都看父母,一住就是好几天。

从廿八都镇出来,我们还去游了邻近的浮盖山。那庄严的仙坛、那迷人的三叠石、那形似的卧牛石、那深幽的石龙洞、那高耸的犁天峰,曾让中国游侠徐霞客在山上转了3天,并为之挥毫写下2000余言的游记尽情赞颂,也让廿八都这个“梦”有了更丰富的诗意。
如果说汪浙成先生是把廿八都写成一个“遗落在大山里的梦”,我就是这个梦的见证者甚至是休憩梦的人。因为看到眼前这一切,让我感到无论是廿八都、江山,还是祖国其他地方,都在发生快速的变化,这变化就像跟做梦一样,让您想也想不到。
“各位乘客,杭州城站马上就要到了。请您收拾好行李,准备下车,欢迎下次旅行再会。”列车女播音员悦耳的声音,把我从美梦中惊醒,我的“梦”又从回到了原点,但决不是终点。因为在外漂泊这20多年的时间里,家乡美丽的山山水水,不知道有多少次出现在我的心里、梦里,是梦把我与故乡时时刻刻牵在一起,永不分离……
 总编辑:徐忠友
总编辑:徐忠友
主 办
浙江省区划地名学
浙江省之江区划地名研究院
-
 保林叔叔讲故事——阿布和希尔
保林叔叔讲故事——阿布和希尔 -
 人间有爱——陈金星医生合集陈金星 小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灸科主任、主治中医师
人间有爱——陈金星医生合集陈金星 小营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针灸科主任、主治中医师 -
 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如何自我调适?本音频由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制作 新冠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不仅严重影响了国民生活,对大众的心理防线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特别推出系列辅助性情绪调节技术,帮助抗击疫情的一线工作者和居家群众们调节心理,维护身心健康。 不同心理状态的人们可以根据自身心理需求进行练习。
新冠肺炎疫情下,心理如何自我调适?本音频由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制作 新冠病毒肺炎爆发以来,不仅严重影响了国民生活,对大众的心理防线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特别推出系列辅助性情绪调节技术,帮助抗击疫情的一线工作者和居家群众们调节心理,维护身心健康。 不同心理状态的人们可以根据自身心理需求进行练习。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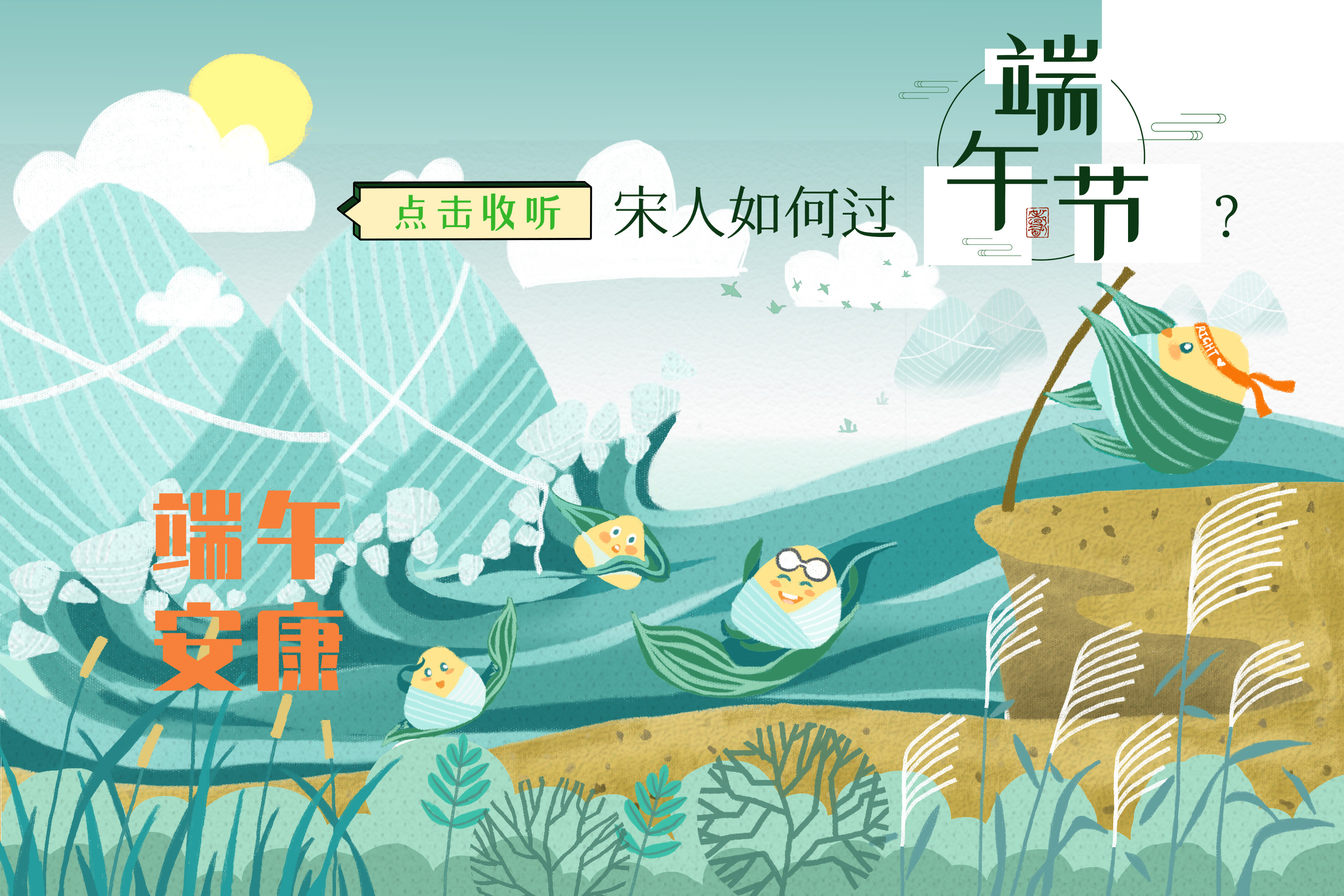 端午安康
端午安康 -
 华语之声祝您中秋快乐!
华语之声祝您中秋快乐! -
 天天读报华语之声、浙江工人日报联合出品
天天读报华语之声、浙江工人日报联合出品 -
 吴芸老师荐好书作者简介: 吴芸,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芸香世界》,作品入选年度散文精选和中学生阅读题库。 2013年,吴芸老师在水秀苑社区成立了“芸文化”工作室。近十年,“芸文化”工作室开展了公益讲座几十个,深受人们喜爱。工作室于2015年被评为“杭州市示范社区学习共同体”。 “杭州市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宣传点是“芸文化”工作室的品牌项目之一,一个点设在西湖区水秀苑社区,另一个点设在“云泊天目”山庄,期望更多人了解与热爱杭城优秀传统文化! 在2023年世界读书日来临前夕,为了与更多读者朋友分享好书,吴芸老师开设“荐好书”栏目。以书会友,共建我们自己的心灵家园!谢谢大家聆听!
吴芸老师荐好书作者简介: 吴芸,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散文集《芸香世界》,作品入选年度散文精选和中学生阅读题库。 2013年,吴芸老师在水秀苑社区成立了“芸文化”工作室。近十年,“芸文化”工作室开展了公益讲座几十个,深受人们喜爱。工作室于2015年被评为“杭州市示范社区学习共同体”。 “杭州市优秀传统文化丛书”宣传点是“芸文化”工作室的品牌项目之一,一个点设在西湖区水秀苑社区,另一个点设在“云泊天目”山庄,期望更多人了解与热爱杭城优秀传统文化! 在2023年世界读书日来临前夕,为了与更多读者朋友分享好书,吴芸老师开设“荐好书”栏目。以书会友,共建我们自己的心灵家园!谢谢大家聆听! -
 心灵花园《心灵花园》是由杭州市上城区红十字会、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和华语之声联合推出的一档关注当代人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的专题访谈节目,每期选取不同的热点话题,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心灵花园《心灵花园》是由杭州市上城区红十字会、浙江省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行业协会和华语之声联合推出的一档关注当代人心理健康和情感需求的专题访谈节目,每期选取不同的热点话题,普及心理健康知识 -
 健康研究所
健康研究所 -
 杭州市组织开展全国爱牙日系列宣传活动
杭州市组织开展全国爱牙日系列宣传活动
